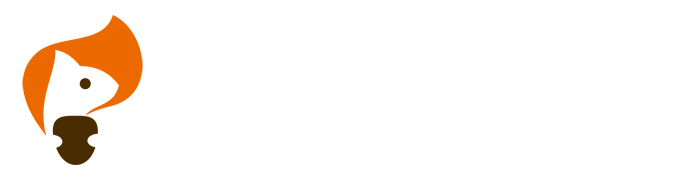玄武门之变后,李世民开启大唐贞观时代,民众渴盼已久的太平岁月,终于再次降临。此前,只有隋文帝短暂实现了统一与和平,但在隋末战乱中,生灵涂炭的景象反复上演。上溯至西晋末年,自八王之乱后的两三百年里,中原几乎就没太平过。
或许李世民与初唐群臣具备了较为清晰的历史断代观念,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:从此开始,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,而对于此前的历史,也要有明确的总结与评判。尤其是天下腥膻的两晋十六国历史,更应该得到一个系统的官方叙述。
十八家晋史的难题
自西晋灭亡后,天下关于谁是正统的问题,一直没有统一意见。没有长期占据中原的政权,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的帝王,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叙述,只能是混乱的,存在各自表述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。
《晋书》监修房玄龄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,他需要从大量晋代史料中找到明确的历史线索,分门别类、有条不紊地来开展编撰工作。房玄龄与编修团队一起,在可见的史书中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,还结合当时官方掌握的其他史料,在适度取舍之后,完成了最终被认定为晋代正史的《晋书》。
李世民点评司马炎
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,在《晋书》上的形象相当包容,威严不足,温和有余,似乎不是一个强悍的开国皇帝,而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推举上位的吉祥物。
李世民对几百年前这位开国君主的评价,却是从仁义角度切入的。司马炎的优柔寡断,在李世民眼中似乎不是缺点:帝宇量弘厚,造次必于仁恕;容纳谠正,未尝失色于人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。当然,睿智的李世民也看出西晋迅速衰败的原因,就在于司马炎不知轻重,舍大取小。明眼人都知道,这是在讽刺他执意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,为八王之乱埋下了巨大隐患。
李世民对此点评道:夫全一人者德之轻,拯天下者功之重,弃一子者忍之小,安社稷者孝之大;况乎资三世而成业,延二孽以丧之,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,畏小忍而忘大孝。圣贤之道,岂若斯乎!虽则善始于初,而乖令终于末,所以殷勤史策,不能无慷慨焉。
《载记》专论异族君主
从历史写作的传承来看,早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,就有《匈奴列传》,并把匈奴君主的谱系,纳入华夏历史叙述的脉络中,是一种史学上大一统观念的体现。而书写两晋史,更加绕不开异族政权的历史了,而房玄龄他们的操作方法,与司马迁如出一辙,将五胡历史纳入官方主流叙事,但区别在于,不会把他们的君主都当成什么华夏正统,非要寻找一个上古圣王作为祖先。
西晋末年,匈奴人攻入洛阳,抢占中原,酿成永嘉之乱。这场祸乱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,也消灭了数不清的世家大族。侥幸逃脱、南渡建康的人们,尤其是读书人,无法接受惨痛的现实,只能期盼北伐成功,夺回故地。
然而,偏居江南的政权,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,只能勉强自保,无力北上,甚至还得不时面对北方异族政权南下征伐的压力。因此,一些知识分子只能选择醉心山水,不问世事,还有人自觉接受异族政权攀附华夏正统的政治论述,哪怕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,但面对艰难的时局,也不得不逼迫自己相信了。
由此产生的用夏变夷观念,在当时十分流行。甚至在用夏变夷观念的逐渐影响下,一些异族政权的君主,发自内心接受了华夏圣贤的教诲,真正开始用严格的圣王标准来要求自己,前秦君主苻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
苻坚: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
然而,苻坚终究不是那个可以一统天下的帝王,淝水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。苻坚兵败后,国内分裂势力蠢蠢欲动,或许苻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,自己会落在曾经信任的姚苌手里。苻坚曾经封姚苌为龙骧将军,掌控兵权,但在自己危难时刻,却被姚苌落井下石。姚苌的权力欲望很大,想取代苻坚成为皇帝,便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。但苻坚却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。见苻坚不肯让出传国玉玺,姚苌便以上古尧舜禅让之事,忽悠苻坚让位。但苻坚的正统观念很深,认为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,姚苌根本不配跟自己提禅让的事。苻坚宁死都不愿意交出玉玺,甚至把玉玺送给东晋皇帝,也不愿意给姚苌,是因为在他看来,姚苌当皇帝并不存在合法性,无法继承大统,连偏安江南的东晋都不如。
传国玉玺象征着华夏正统,得到它的君主,才真正拥有了天命,在乱世更是如此。不过,姚苌等叛乱者并不会因为缺乏正统就不去争权夺利,他在杀害苻坚后,建立了后秦政权,好不容易由前秦短暂统一的北方,再次陷入兵荒马乱。《晋书》记录的割据政权,大多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夜空,匆匆降临,又转瞬即逝。